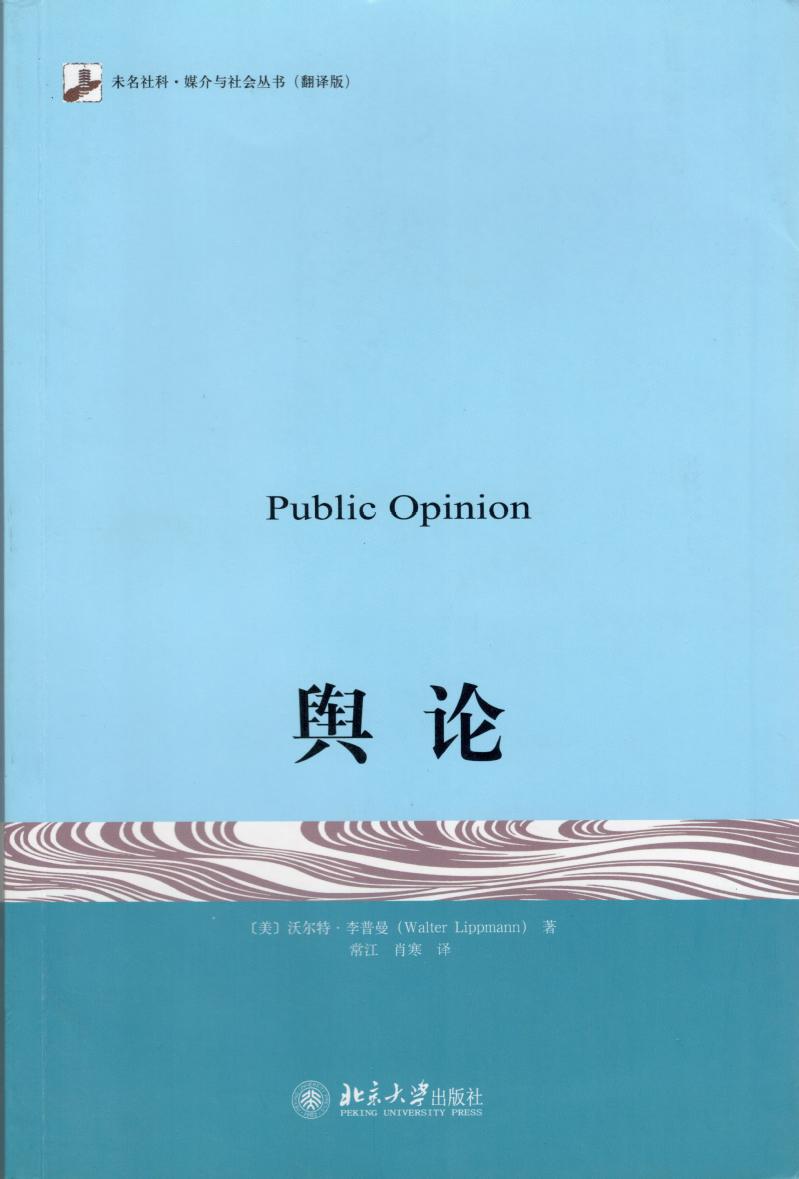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公共舆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对公共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自1922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其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它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舆论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公共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该书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首次全面论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书评:
看到北大版李普曼近百年前名著 Public Opinion的新译本很高兴,因为埋在心头多年由于翻译不准确带来的学术纠结这回解开了。这个译本从标题到内容,翻译得相当正确;书的编排吸引人,利于读者快速把握要点。
1980年我读到林珊老师的内部油印译本,书名叫《舆论学》,1988年正式见书还是这个书名;2002年获知有了新译本,一看书名《公众舆论》,这不是同义反复吗?翻译不是小事,特别是书名和书中的关键概念必须准确。课堂上我讲述书中李普曼的几个关键概念,学生在译本里找不到对应词;书的标题使得“公众舆论”这一不正确的表达充斥于每年数千篇学位论文。翻译对学术的推进或滞阻可见一斑。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李普曼以自身的体会与感悟,生动描画了“舆论”的现实及其困境,将政治学中的这个规范性概念,转换为其实践如何是可能的这一经验问题,开启了舆论研究的新面向。
该书自1922年首次出版以来,影响始终不衰,成为不同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奠定了大众媒介研究的基础,为宣传分析、舆论调查、把关人、议程设置、接受效果等研究开了先河。恰如有学者说的,大众传播的研究大多不过是李普曼《舆论》的注脚。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摘录:
现在,我们不妨将刚刚提到的灯柱下的四人置换一下,将其想象成政府、政党、企业、社会、群体、商界、业界、高校、党派、国家等。想想正在就一项可能影响到很多人的法规进行投票的立法者,以及正在做出决策的政治家;想想正在重新划定欧洲版图的巴黎和会,在会上同时揣摩着母国政府和出使国政府意图的大使,在欠发达国家争取特许权的开发者,呼吁发动战争的报纸编辑,请求警方限制娱乐活动的牧师,决定发起罢工的俱乐部酒廊,谋划对学校进行规制的缝纫妇女会,正在裁决俄勒冈的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决定妇女工时的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否承认某国政府进行决议的内阁会议,抉择竞选人或起草纲领文件的政党集会,2700万正在投票的选民,惦念着某个贝尔法斯特(Belfast)爱尔兰人的科克(Cork)爱尔兰人,谋划着重建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共产国际,应付着雇员的一大堆要求的董事会,正在择业的青年男子,正在估算下一季度供求量的商人,正在考量市场动向的投资人,正在思虑是否应给一家新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家,广告商,广告受众……在不同的美国人眼中,“大英帝国”“法兰西”“俄罗斯”“墨西哥”这些概念的含义可以千差万别。这样的差异性和切斯特顿先生列举的豆绿色街灯下那四个人的情形,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过,暂且不要忙着分析人与生俱来的错综复杂的差异性。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充分地意识到每个人对于其所处世界的认识都是差异显著的。当然,我毫不怀疑作为动物的人类的不同个体之间必然存在显著的生理差异——没有才怪。但是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其对于环境做出的反应。作为一种拥有理性的动物,在尚未确定行为环境具有值得衡量的相似性的前提下,就先去总结行为的相似性,此类做法实在过于浅薄。
人们对于天性与后天教育,以及先天品质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上述观点的实际价值就在于对这一争论做出了十分必要的改良。因为“拟态环境”概念的提出,正是对人的天性与环境条件两者加以综合的结果。仅凭对人的行为的观察,便去斩钉截铁地描述人的本质、预测人的未来,甚或试图直接归纳社会的基本环境条件,都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拟态环境”的概念可以表明这种夸夸其谈的无效性。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人对于宏大社会的事实信息会做出何种反应,我们所知的仅仅是人对于宏大社会中的某个极其有限的片段图景会做出何种反应。基于有限的事实材料,我们既不能就宏大的社会环境得出任何概括性的结论,也不能对人本身得出任何概括性的结论。
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下去。不妨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都非基于直接的、确定的事实信息,而是基于由其意识加工出来的关于事实的图景,或由别人向其传递的此类图景。例如,若某人拥有一本地图集,且这本地图集告诉此人世界是一个平面,那么他就一定会避免在行船中驶向假想中这个平面的边界,因为他担心会“掉出去”。若某探险家在地图上看到某处有一眼可以令其永葆青春的泉水,那么他便会踏上寻找这眼泉水的旅途。若某人挖掘出了在其看来像黄金一样的黄色的东西,那么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黄金。人在任何时间点上的行为都是基于其彼时彼刻对于现实世界的某种想象。这种想象能够决定人们为何事而奔忙,产生何种情绪,怀揣何种希望,却无法判定人们最终会取得何种成就,以及事情将会迎来何种结果。
如果我们试着用趋利避害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生活,便很快会发现这种享乐主义的思路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使我们假定趋利避害就是人的社会生活的目标,那么人们何以认定某种方式就一定比另一种方式更“趋利避害”呢?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是通过道德感的指引吗?那么为什么人会持有某种特定的道德感呢?又或者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利己心理来解释?那么一个人是如何确定什么才是自己所追求的利益的呢?又或者可以用人对安全感、名誉、支配权或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含义其实比较模糊)的追求来解释?可是人们又是如何认定何为安全感、名誉、支配权,以及如何确定自己想要实现何种自我呢?毫无疑问,快乐、痛苦、道德、成就、守护、提升、征服,都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解读。人的本性之中存在对于这些目标的趋向性。但是对于这些目标的表述以及对于这种趋向性的描述,并不足以解释作为结果的人的行为。人们常常进行推理,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拟态环境——现实世界在他们头脑中的再现——是其思想、感情、行为的决定因素。因为假如现实与人对现实做出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并非间接且基于推断,而是直接的、毫不迟延的,那么便不会存在犹豫不决或判断失误,萧伯纳(Bernard Shaw)也就不会说“除了作为胎儿在母亲腹中的那九个月,人对自身事务的料理还不如植物”(因为我们无法像子宫中的胎儿那样贴切地融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摘编人:陈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