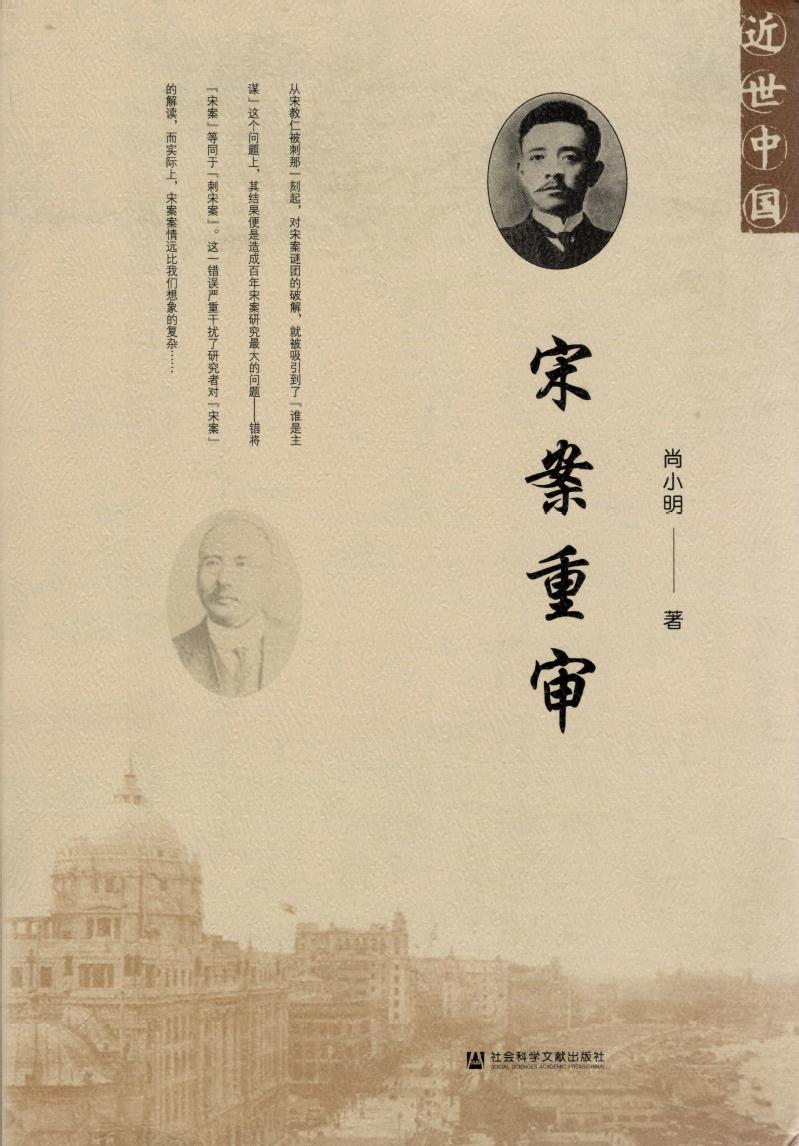
内容简介:
百年宋案研究首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初政坛秘辛,对案件发生前后的许多矛盾现象也都给予了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全书约有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书评:
穷数年之心力,博观群览,几将相关史料搜罗殆尽,并深探语境,精析文本,逐字逐句,力钻词义,于错综纠结的史料之中,考校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抽丝剥茧,终使案中案外隐情,一一再现。
——刘桂生
我们似乎可以在尚小明的《宋案重审》中读到另外的意味,那是聚光灯下真相难寻背后的民初政治风云,正是那段历史中的波与诡谲造成了各方都仿佛成为了密室杀人的嫌疑人,那些我们今天在课本和小说中读到的历史人物,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多面性。
当我们重审一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对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历史人物的一次再认识,更是对我们自己如何知事识人的一次再升华。正是在这样的意味中,我们才发现在对宋案的重审过程里,那些我们本以为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正在展现其复杂的一面,这其实对我们未来以更加客观全面的视角进行历史阅读和研究是很有益处的。
——豆瓣网友 宝木笑
摘录:
读完书稿,我觉得该书不仅为实事求是澄清宋案真相提供了较充分的史料、史实和分析、论证,而且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能给人不少启示。例如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加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
还如必须追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摸清历史人物之间真实关系。如书中强调,宋案不等同于刺宋案,它是由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分歧,袁世凯有意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鼓励纵容洪述祖、应夔丞打击宋教仁,洪应两人图谋诬宋、刺宋邀功牟利,以及刺宋后各方反应、案件审理、诸凶犯下场等一系列环节构成,而其中许多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互相关联的,如果孤立考察刺宋一事,则难以认清全案的内幕与真相。
宋案发生已逾百年,百余年来,无论专业史学研究者,还是普通文史爱好者,对宋案真相的探究从未停止过,并且有愈来愈热之势。照理,历经百余年探究之后,宋案细节应当愈加清晰,离真相揭露应当愈加接近。然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时至今日,宋案探究至少存在四大问题:一是严谨的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二是案情分析严重简单化,三是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四是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研究者利用。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严重问题,宋案探究非但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而离真相越来越远,甚至出现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等问题。因此,宋案探究已到了需要彻底清理并切实向前推进的时候。
在洪、应的构陷计划中,还有一点须格外注意,即该计划的诋毁对象虽然包括孙、黄、宋三人,但很显然,孙、黄只是陪衬,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主要是在宋教仁积极努力下完成的,其后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社会事业”,黄兴亦一度担任湖北铁路督办。唯有宋教仁仍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运动,大力宣讲其政党内阁主张,并为国会选举奔走呼号,舆论至有“在革命时代,宋实不如孙、黄,而在政党时代,虽孙、黄实不如宋也”之说。应夔丞特别告诉赵秉钧“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暴露无遗。在应夔丞看来,宋教仁是赵秉钧保住总理位置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不惜虚构事实,特别提出此点,欲以此来激刺赵秉钧。……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原电所用乃“燬”字,而非“毁”字。张永和芦笛用“毁”字解释“燬”字,完全不具有说服力。洪述祖试图将“燬”“毁”二字混为一谈,也是狡辩。……洪述祖在3月13日电说出“燬宋酬勋位”之前,已经于3月6日函中以“除邓”并“登其死耗”为例,向应夔丞明白指出对宋“乘机下手”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因此,此处“燬宋”指杀宋已毫无疑义。倘若“燬宋”是指损毁宋之名誉,则此处便不需要讲“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因为自2月2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冬电”以来,洪、应二人早就在谋划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了。所谓“相度机宜”,其实是与3月6日函中“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相呼应。因此,“燬宋酬勋位, 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其实是洪述祖更明确地向应夔丞下达了指令:如果宋有“激烈之举”,就可“乘机下手”,条件是酬应以“勋位”。这样一来,宋教仁的命运就主要掌握在了应夔丞手中,因为,何为“激烈之举”,何时“乘机下手”,就看应夔丞如何判断了。当然,京师高等审判厅也没有采纳洪述祖的诡辩,二审判决书写道:……
毋庸讳言,袁世凯对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政府,并宣传其政党内阁主张,心有不满;袁世凯指使洪、应构陷“孙黄宋”,以损毁其声誉,亦为事实,但他却没有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党领袖的想法。故当洪述祖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以警其余时,遭到了袁的反对。袁明确表示此种做法“实属不合”,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洪的建议。洪述祖所谓“燬宋酬勋位”,不过是其假托中央名义以“虚名”诱应杀宋的诓骗之举;洪述祖所谓“债票特别准”,也不过是其在“虚名”诱应无效之下,假托中央名义以“实利”诱应杀宋的又一诓骗之举。
但问题是,应夔丞也为洪述祖所骗,始终以为杀宋是中央的意思。应之所以信洪,与洪的特殊身份和过往的表现有关,“超然百姓姚之鹤”有段话讲得最有说服力。他说:盖洪犯之所以取信于应犯者,其资格则内务部秘书长也,其历来函电则均称奉有命令也,即此已足坚应犯之信心矣。而又况介绍赴京谒总统、叩总理,代为谋干一切,悉有事实为之证明。此洪犯之所以驱策应犯者在是,而应犯之所以甘为洪犯鹰犬者,信洪犯并信洪犯之确能直接政府也。
武士英,即吴福铭,又作武复民、吴发明,山西平阳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时年22岁。据其口供,曾在贵州某学堂肄业,后充云南巡防营第三十营哨官,案发前在上海以售花瓶为生,住五马路六野旅馆(又作鹿野旅官)。在刺宋之前,穷愁潦倒的武士英因为即将获得应夔丞的千元赏金而忽然举止怪异,“得意忘形”,以致同住六野旅馆者目之为“神经病”。迨宋教仁被刺身亡,黄兴等发出重金赏格后,旅馆中人忆及武士英之前举动,觉得可疑,遂报告于国民党人陆惠生,从而为破获刺宋案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
应夔丞于武士英被捕前半日,即3月24日凌晨被抓获。他在预审时,也承认武士英于行刺宋教仁当晚曾到其家,为其留住。不过,应夔丞辩称,武士英是受人指引来到其家,他将武士英留住是为了先稳住武士英,然后“禀明上官”。应夔丞并供称,他曾对武士英说:“你能到英国读几年书,脑筋就更清楚,你若外出,可不得了。”此点与武士英所供正相印证。经租界公堂预审之后,4月16日武士英被法捕房移送上海县模范监狱监禁。4月18日晨,上海地方监察厅长陈英派司法警察四名,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派副官吕翊率军士两名,会同护送武士英至海运局步兵六十一团营仓禁锢,与应夔丞分别管押。然而,仅仅一周后,即4月24日上午,武士英突然死于营仓之内,在当时引起诸多猜测,成为案中疑案。
国民党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依然发起革命,就是要及早割掉“伏在北洋军阀里面”的“小痈”,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以免等到“大溃烂”的时候“无从施治”,这就是“二次革命”的意义所在。这一意义并不因革命失败而减损分毫,恰相反,袁世凯后来逐步走向帝制,以及袁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反复证明了当初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想割掉北洋军阀里的“小痈”是很有远见的,只不过因当时所谓“国民”尚未觉醒而遭到失败。
我们不应当因为袁、赵不曾主谋刺宋,便否认“二次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贬低其意义。与其苛责国民党不走所谓“合法”道路,不如探求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国民党再次走上“革命”道路。
(摘编人:韩海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