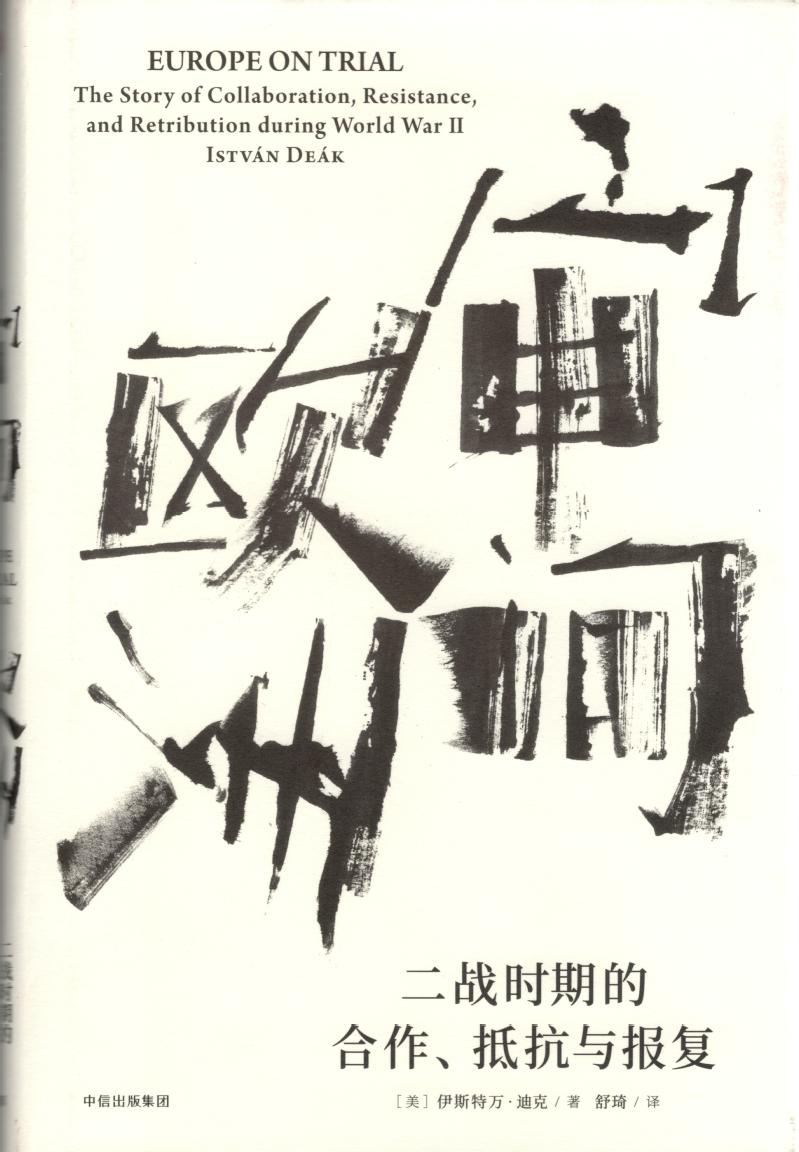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德国纳粹,“二战”时的欧洲不论是国家政府、地方机构,还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机下,选择被动顺从、主动合作或是奋起抵抗。
在本书中,广受称赞的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作者通过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考察了这三个主题。他们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是与占领者合作呢,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幸存呢,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抵抗者呢?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
作者讨论了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对那些切实的或可疑的战争罪犯以及战时合作者的肃清,这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暴力、驱逐,以及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法庭上进行的司法审判。本书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战时和战后的种种道德因果。
书评:
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
——斯坦福大学东欧史讲座教授 诺曼·M.奈马克
迪克是东欧和中欧研究的伟大开拓者……在这部书里,他汇集了大量占领时期的道德难题,就像那些杰出的人如斯托拉以及不是那么勇敢的大多数人所遭遇的一样。它联结起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对立双方的经验:东方和西方,被占领方和合作方,以及左派和右派。他的主要案例都关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来被削弱时,欧洲情愿与纳粹势力达成和解。一个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们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本书指出,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是此岸。
——耶鲁大学东欧史教授 蒂莫西·斯奈德
伊斯特万·迪克带领读者对欧洲历史上一段黑暗岁月的一些最黑暗的方面进行了全盘检视。他绝不迎合民族神话和未经检验的关于民族美德的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迪克所写的,是人类给自己造成的大灾难之一。书中诸多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和令人深感悲痛的行为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
——《纽约书评》
摘录:
当地居民想要在外国军队占领中活下来,除非占领军军纪严明,也就是说,士兵遵守本国的军法,而且把当地人视为自己的人类同胞,不随意轻视。作为回报,占领军也有权期待当地人会服从那些至少还算合理的命令。而且不会威胁到士兵的性命。没有一部军法,包括纳粹军法,会容许士兵抢劫或屠杀无辜平民。事实上,1943年10月出版的德国刑法典小册子第211条就规定,对犯下谋杀罪的士兵要处以死刑,无论受害者的种族、宗教信仰或国籍是什么。……“二战”期间德国部队在东欧和东南欧的滔天罪行表明,如果指挥官不肯费神来执行军法典或是有意忽略,那军法典就形同虚设。
可惜,这种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相互尊重的理想模式只在历史上断续存在过,大多数情况下,军队里都是一帮不守规矩的人,他们来到外国土地上,无论当地人是“友好”还是“敌对”,他们只会在这片土地上散布暴力和劫掠。……
德国的胜利把顺从、合作与抵抗的问题带到了巴尔干半岛,但是西欧、北欧不同的是,这里的局面生出更多事端。其中一个事端就是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海岸附近通常有一些尚未开发的山地和无数的岛屿,这就给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半合法和非法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空间。另外一个事端就是巴尔干的居民不同于丹麦人或荷兰人,他们不是爱好和平的人,数百年来的战斗,无论是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者的,还是反对他们的,都教会这里的人一件事——这个世上能够相信的,只有手中的武器、自己的家庭和部族。但主要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多样性。……
1941年4月,南斯拉夫军队瓦解,部分原因是极端主义的克罗地亚政治家利用德军的到来,宣布成立一个克罗地亚人的法西斯国家。就像“一战”末期奥匈帝国军队的士兵所经历的一样,战败后,南斯拉夫军队很大一部分被俘的士兵恍然大悟,他们竟然成了敌军的同盟,是胜利者。
我的观点是,正如大多数报刊文章和一些历史研究文献所称,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远非德国希特勒的傀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命运由自己主宰。此外,这些盟友还启发了被德国打败和占领的若干国家,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希特勒的欧洲保住自己的主权地位,这恰恰就是德国盟友所享有的待遇。结果,像捷克保护国、丹麦和法国这些被德国打败占领的国家,与德国的盟友之间,往往变得很难区分。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包括一些被占领的国家,在整场战争中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从而能够严格控制国内右翼的亲纳粹反对派。还有,他们会自主决定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执着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基本上也能决定与亲德邻国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德国纳粹形同被架空。换句话说,德国在欧洲推行的政策,往往都是本末倒置。
关于德国的正式盟友,我们可以简略总结出以下四个观点:首先,德国的同盟体系模糊混乱,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第二,德国盟友的独立性,给了他们自主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领袖和公民要为自身所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第三,德国很多盟友彼此敌对的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第四,德国的盟友把战争当作有利的工具,来剔除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换言之,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
在罗马,有三支主要力量在开展大量反纳粹抵抗运动: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巴多格里奥),温和派(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君主主义者支持重建战前的政体,但要把法西斯党剔除在外,温和派想要民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不过,各方都接受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证明意大利无罪,或者至少要弥补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巴尔干半岛犯下的罪行。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共产党,同盟国在安齐奥登陆后陷入艰苦鏖战,便对游击队施压,让他们去攻打德军,在盟军的激励和助长下,共产党甘冒风险。
凯塞林的建议被采纳了: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就拿10个意大利人的性命来偿。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中校起初希望只处决死刑犯。结果只找到4名意大利死刑犯,所以目标群体不得不扩大,就把政治犯、普通刑事犯、拉塞拉大街围观的人、意大利战俘(包括一名将军)和78个犹太人都算进去了——他们辩称反正犹太人怎么都已经被宣判死刑了。……
世界大事,尤其是“冷战”,把公众注意力从惩罚战犯上转移开,这样的局面至少持续到1960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在阿根廷抓捕和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并运至以色列。两年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和判刑,并被绞死。艾希曼审判激发了一系列的诉讼,其中就包括在西德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1963-1965)。同样重要的马赛尔·奥菲尔斯的电影《悲哀和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这部坦诚而颠覆的电影于1972年问世和上映,讲述了迄今为止在一个中型城市里法国人与德国占领者超乎想象的合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人的合作与抵抗,以及欧洲国家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应承担的责任,这两个问题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对这两个问题的重新审视才徐徐开始。一些曾经逃脱审判的个人才又站到司法的门口,只是对他们的审判和复审一直拖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对这些人的指控总是归到反人类罪,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只有这条罪行不会因为时间而失去法律效力。
(摘编人:韩海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