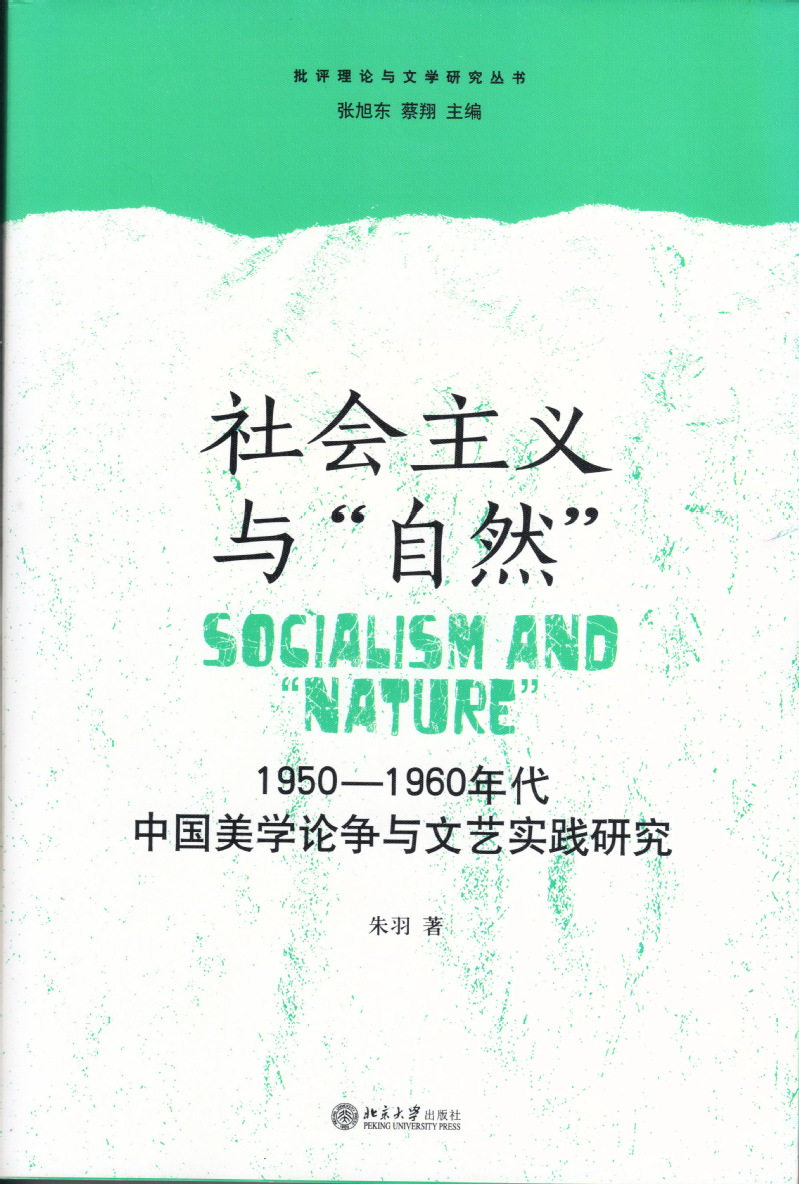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尝试从自然出发重构1950—19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治,所采取的具体路径是: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195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继续改造内外自然这一历史时期,以此一时期涌现出的新山水画、大跃进民歌壁画、自然美的争论以及社会主义新喜剧等文艺、美学实践为具体对象,考察其所呈现的独特文化-政治经验(国家建设、新人培养等)。在“自然”这一核心范畴下,本书将看似零碎、分散的文艺实践与美学论争重新整合在一起,使之呈现出“文化政治”的广度与强度,并在理论与历史两方面获得意义的伸展:首先呈现隐藏在各种文艺实践与美学论述背后的核心线索——“自然”的重建(从外在的自然形象及其意义,到人的“自然本性”,再到作为“第二自然”的风俗世界的建构);其次追问这一重建过程遭遇到何种根本难题,以及这一难题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复兴有着何种启示性意义。
摘录:
简言之,作为自然界的“自然”首先是劳动的对象,但在自觉的“革命”之前,生产、生活进程必定已经处在某种“自然状态”之中。它规定着已有的“人性”,具有一定的“自发”特征,同时受到如同“自然规律”一般的经济规律的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非只是改造其中某一个方面,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改造。因此可以说,改造“自然”始终贯穿于毛泽东所谓“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虽说在“显白”教诲中,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采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自然”观,然而在具体的运作中,它无法回避甚至是主动吸纳了这一具有深厚伦理与政治内涵的“自然”概念——自发、自因、根源、本性——及其所指向的问题领域。
激活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概念,与恰当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创造性,有着相当微妙的联系。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自然”议题之所以显得缠绕、繁复,就是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一动态性三元构造。
历史语境的变迁使“山水”的功能发生剧变,而新中国的成立其实赋予了“山水”重生的契机。
“新山水画”实践带来了一种具有意义深度的“自然-历史”形象,同时也可以说构造出某种新的“视觉世界”。随着新中国生活世界的逐步确立,重建自然的意义变得十分关键。而山水画改造实践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质。
在社会主义山水与风景的多重表征之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少数民族的生活世界以及相关叙事性作品的出现,尤其是由“边疆”这一概念所指示出的“风景”问题,一方面与上述“自然”表象有着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生成了自身的问题架构与难题结构。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自然形象首先是政治性的。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美学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处理“感性的”政治。
劳动与政治之间“断”“续”问题标示出今日文化政治的真正难题之一。
“大跃进”中干劲冲天的劳动主体同自然斗争的场景在“新民歌”和“新壁画”里有着集中表现。
如果说克服工农群众臣属性的冲动始终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史之中,那么“大跃进”实践则为之赋予了别样的广度和具体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劳动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生产问题,它必然会受到政治、伦理的渗透,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问题。
“大跃进”群众文艺创作“模仿”了劳动生产的节奏,它本质上不是以“作品”而是以“生产”为尺度的。这就造成了“量”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质”。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氛围中,在全国快速完成人民公社化的转型之中,在高速度、高积累的发展模式下,毋宁说“大跃进”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地将“时间”意识即“新与变”贯彻到普通劳动群众意识之中的集体实验。
“笑”的现象提示出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人的改造的某个重要维度。……“笑”与“放松”之间微妙的关系,与人的日常状态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与“新人”的行动、心理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探讨。
歌颂性喜剧试图召唤一种“崇敬的笑”,实际上是旨在召唤一种新的观众,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一种新的“内在自然”。这才是社会主义喜剧的教育本质所在。但是当时的批评话语难以在喜剧主体和此种理想的“笑”之间建立现实的、具体的关联,毋宁说只是提供了一种颇为主观的设想或者说“设定”。
如果新相声只是围绕“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这一轴心展开,其自身的喜剧性教育经验就会相应减弱。社会主义政教美学话语无法把握的,正是这一无法完全被同一化的“革命-分心”经验,它自然也无法完全解释此种蕴含于社会主义喜剧文化内部的矛盾-动力结构。
从新中国心理学发展史来看,自1958年以后,心理学界就着力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关的劳动、医学与教育心理学;但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中性”专业领域,尤其是在“中间科学”这一相对“暧昧”的界定下,缓冲着显白性“政治”教导的全然渗透。
中国社会主义最激动人心之处,便是试图在“匮乏”之中克服“匮乏”本身,通过扬弃“物质刺激”,重新建构概念、意义与感觉之间的联系。其中关键之处又在于用“不断革命”这样一种诉诸“未来”的方式——同时也扬弃了一种铁律般的、宿命的未来,在生产过程中改造“生产”本身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改造“日常生活”本身的构造。此种文艺实践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加速”,也宣告了旧有杂糅“物质刺激”的合作化叙事向扬弃“物质刺激”的路径转化。
当下的知识生产需要勇于去重建一种总体性,即在历史的结构性难题、治理理性的历史位置、诸领域的“文化”表述,与真正“自觉”的政教机制之间重建一种关系。此种重建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都将成为革命的20世纪获得其后世生命与自我意识的契机。
(摘编人:彭雪勤)


